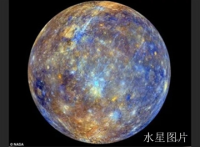理想国按:
说来可能奇怪,作为一个直男,主页菌最喜欢的宋代词人,可能是李清照。
她年轻时与赵明诚的爱情故事,她前后判若云泥令人唏嘘的人生际遇,她作为有宋一代无可比拟的第一才女,这些都是理由。
但最重要的,是从她的诗词里透露出的亦婉约清丽亦阳刚傲气的心性品格,以及她在生命晚年的孤苦伤痛之中,依然遮挡不住的风流高贵的生命底色。
今天微信,和你分享作家李劼在《唐诗宋词解》里写李清照的篇章。
李劼论唐诗宋词,其立论在“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对照李清照的人生和诗词,不可谓不精辟透彻。
南宋以降,词人如倦客思家
文:李劼

周邦彦晚年曾有一曲《西平乐》,描述金兵南侵之后的苍凉和感慨:
元丰初,予以布衣西上,过天长道中。后四十余年,辛丑正月,避贼复游故地。感叹岁月,偶成此词。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追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敧斜。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
此曲可作地标看。其地标意味在于,标出了北宋词与南宋词的界分。借用该曲辞语,宋词在北宋年间犹如朱颜翠发,及至南宋以降,词人好比倦客思家。
用西方文化的经典话语来描绘便是:北宋时代是词人的乐园天堂,琴书欢乐,风流倜傥;蛮族南侵,不仅京都沦陷,一众士子也随之被逐出《清明上河图》所描摹的繁华盛世,所有词家都不得不坠入失乐园的境地和年代。

整个宋词庶几成了李后主身世的翻版,由当年东京的雕栏玉砌,变换成了南渡之后的断壁残垣。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北宋词风好像是后主宫廷时代那股风流乐逸的续篇,以柳永词为最;而南宋词风则仿佛后主身陷囹圄之后的离恨孤愁,有易安词为证。此三者乃是长短句自晚唐《花间集》之后在艺术成就上的三座高峰后主,柳永,李清照。
就人生经历而言,李清照与李后主相近。李后主的婉约之中有着观音般的慈悲,温婉如水;李清照的如泣如诉背后,却是山一般的凝重,峻峭嶙峋。李清照的阳刚气度,绝非大家闺秀可以形容。

不过,那样的阳刚,并非见诸其词,而是洋溢在其诗作里。早在少女时代便锋芒初露于《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那两首和诗起笔仿佛利剑出鞘:“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更不用说其间的凌厉犀利:“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
如此的不依不饶,晚年飘零之际依然壮怀如故:“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尤其是“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直截了当地感慨朝中无人,故而只能怆然“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李清照忧国如是,悼亡亦不作小女子泣:“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倘若倒过来,让李清照先行,赵明诚悲泣,恐怕未必能够写到如此沉郁的境地。那位夫君赠与爱妻的评价乃是“清丽其词,端庄其品”。“清丽”一辞,并非易安词作的写照。
这对琴瑟和弦的夫妇,表面上夫唱妇随,实际上却是夫随妇行。曾有《清波杂志》记载:“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
 最照见易安心胸的两首诗,一首颂项羽,一首赞嵇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
最照见易安心胸的两首诗,一首颂项羽,一首赞嵇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
几千年的历史书写传统是成王败寇。混混刘邦得了江山,被尊为高祖;贵族项羽败北,成为“虞兮虞兮奈若何”的笑料。至于嵇康,更是让一班酸腐儒生谈虎色变。易安的直抒胸臆,气度非凡。
论史也罢,说词也罢,易安都是居高临下,全然巾帼不让须眉的傲气逼人。短短一篇《词论》,从开元、天宝年间说起,历数诸多词家,没有一个放在眼里。
有的是一语中的,比如,秦少游“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鲁直“即尚故实,而多疵病”;但也有失之盲目,比如非议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尤其是填词在有唐士子间初兴,竟然被易安讥为“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此刻的李易安,似不像是项羽、嵇康的力挺者,而俨然一大家闺秀也。
不管怎么说,易安女士总该记得,当年也是撒过娇发过嗲的人儿:“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就算这并非郑、卫之声,但易安的那首《醉花阴》似乎也是风情万种的噢: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赵明诚的“清丽其词”,想必是由此生发的。其实,真要说清丽其词,易安少女时代轰动京城的《如梦令》倒是恰如其分: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小荷初露,清新亮丽,而又不失端庄。即便做了少妇之后的思念夫君,也依然含蕴如故: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纵然是“念武陵人远”,照样“欲说还休”。只是凝眸之际,又添“一段新愁”。如此心绪,与其说是丰富,不如说是曲折。秦少游词也曲折,但没有这般真切。难怪易安会说秦词“少故实”。易安如此故实的这般切身体味,最是见诸那首《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阕的“罗裳”、“锦书”、“月满西楼”做足了铺垫,下阕将飘零付诸流水,将相思分作两处;最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用字轻盈,思绪凝重。
从眉头到心头,仿佛是很随意的起落,却言犹尽,思无断,绵绵如流水,水中见落花。仅此一曲,便可见出易安词作的功力之深湛。正如后主词作前期、后期无有高下之分,易安南渡前后的词作也当作如是观。
不过,易安词作也并非每首都能如此精湛。相比之下,这首《蝶恋花》显得轻浅一些,仿佛春天里两声清丽的娇嗔:
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
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
假设李易安没有经历丧夫和离乱,其填词也就仅止于一介才女的尽情尽兴发挥。尽管其才华已然举世无双,但其词作只能让人会心一笑,不至于让人五内俱焚。南渡前后的词作,在艺术审美上无有高低之分,但在阅读效果上却轻重分明。
李易安孤身流离到南方的岁月,与当年在东京城内新婚燕尔的欢乐时光相比,反差大得触目惊心。而易安以什么样的心境填出这首《永遇乐》,也就可想而知了: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最后一句的经历沧桑,令人震撼。

上阕以“谢他酒朋诗侣”作结,可以说心高气傲依然如故,也可以说于南宋王朝心灰意冷,故而将香车宝马拒之门外。须知,香车宝马,酒朋诗侣,在易安是谢拒得非常彻底的,以致最后孤身独处到了令世人不知其所终的境地。其孤傲,其自尊,跃然纸上。
此曲下阕以遥忆“中州盛日”起笔,甜蜜之中充满酸楚。想着想着,结果是不忍想,更不忍看自己,只能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凄凉得惨不忍睹。有着如此沉痛的故实,在《词论》里责少游一句“少故实”,假设秦观有知,也只能认了。
南渡后的李易安,犹如亡国后的李后主。填词与其说是乐趣,不如说是孤苦无告的泣诉。或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或者“挪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然而,不管再憔悴,再风鬟霜鬓,易安也像后主一样地照样从容端坐,从不粗头乱服。有《孤雁儿》为证:
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里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读到“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时,蓦然想起的,是李后主的《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同样的痛心彻骨又同样的孤苦无告。国亡也罢,家破也罢,造成的伤痛都是非常个人的,而不是群体的,并且不以个人的身份地位为转移。

君王也罢,才女也罢,伤痛是一样的伤痛,孤苦是一样的孤苦。再加上彼此心灵的同样高贵,彼此才华的不相上下,几乎就是一曲曲等量齐观的遥相酬唱。李后主有《虞美人》如彼: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易安有《声声慢》如此: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遥相对应的两座词作艺术高峰,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都是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都是登峰造极的身心俱境。
韵律的完美,辞句的色泽,心绪的起伏跌宕,节奏的柔婉激越,更有那令人扼腕的身世,令人震撼的悲切,回肠荡气之际,惟有怜悯却了无仇恨的慈悲,所有这些审美意境,皆足以让自以为是的词家词作黯然失色,也让千年来的诸多词学家们不知所措。就算他们也曾竞相喝彩,也不知彩在哪里。

读着易安如此这般的巅峰词作,其《词论》中的居高临下,目空一切,也就只能默认了。艺术,毕竟不是体育竞技。尤其是身心俱境之作中的故实、情愫、优雅的辞句、高贵的心胸、悲悯的气度,都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瑰宝。
词乃情物,然情至深处的巅峰词作,却各相异趣。李后主是平心静气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易安是泣不成声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再顺便说一下,柳耆卿是无可奈何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位词家之中,耆卿最为性情,后主最是平和,易安最易动容,洞幽烛微地感受着晚晴寒透的飘零人生。
高贵,在李后主是悲悯,在柳耆卿是贵己,在李易安是自尊。三者的词作共同推出的,乃是人的尊严。无论是亡国之君,还是江湖浪子,抑或流离贵妇,都不约而同地在朝廷、庙堂、战乱面前,独立不羁,我行我素,我吟我词,我书我心。这是三者词作的底气所在,也是三者词作的审美底蕴所在。
(上文选自《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理想国2018年1月)

《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
李劼 著
重返唐诗宋词,一言以蔽之:诗为心声,词乃情物。诗言者,心声也,自《诗经》始。唐诗最为可观之处,就在于如何从初唐气壮如牛的言志,演变成晚唐温柔婉约的抒情。无情,则无词。
北宋之词,情盛,所以有如水草丰茂;南宋之词,两安之后,日渐枯萎。一部《人间词话》,最令人感慨的致命伤在于,不知词为情物。就唐诗宋词阅读的审美观念之改观而言,本著只是开了个小小的口子。雾霾尚未清除,世人还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