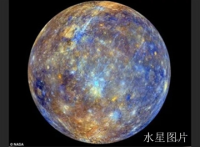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易安有《声声慢》如此: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遥相对应的两座词作艺术高峰,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都是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都是登峰造极的身心俱境。
韵律的完美,辞句的色泽,心绪的起伏跌宕,节奏的柔婉激越,更有那令人扼腕的身世,令人震撼的悲切,回肠荡气之际,惟有怜悯却了无仇恨的慈悲,所有这些审美意境,皆足以让自以为是的词家词作黯然失色,也让千年来的诸多词学家们不知所措。就算他们也曾竞相喝彩,也不知彩在哪里。

读着易安如此这般的巅峰词作,其《词论》中的居高临下,目空一切,也就只能默认了。艺术,毕竟不是体育竞技。尤其是身心俱境之作中的故实、情愫、优雅的辞句、高贵的心胸、悲悯的气度,都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瑰宝。
词乃情物,然情至深处的巅峰词作,却各相异趣。李后主是平心静气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易安是泣不成声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再顺便说一下,柳耆卿是无可奈何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位词家之中,耆卿最为性情,后主最是平和,易安最易动容,洞幽烛微地感受着晚晴寒透的飘零人生。
高贵,在李后主是悲悯,在柳耆卿是贵己,在李易安是自尊。三者的词作共同推出的,乃是人的尊严。无论是亡国之君,还是江湖浪子,抑或流离贵妇,都不约而同地在朝廷、庙堂、战乱面前,独立不羁,我行我素,我吟我词,我书我心。这是三者词作的底气所在,也是三者词作的审美底蕴所在。
(上文选自《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理想国2018年1月)

《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
李劼 著
重返唐诗宋词,一言以蔽之:诗为心声,词乃情物。诗言者,心声也,自《诗经》始。唐诗最为可观之处,就在于如何从初唐气壮如牛的言志,演变成晚唐温柔婉约的抒情。无情,则无词。
北宋之词,情盛,所以有如水草丰茂;南宋之词,两安之后,日渐枯萎。一部《人间词话》,最令人感慨的致命伤在于,不知词为情物。就唐诗宋词阅读的审美观念之改观而言,本著只是开了个小小的口子。雾霾尚未清除,世人还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