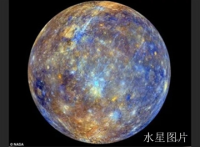诚然,我国古典诗词,以思妇、言情为题材的很多,也不乏优秀作品。唐诗中有王昌龄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等等。唐宋词中这类作品就更多了:王建《宫中调笑》里的“杨柳,杨柳,日暮白沙渡口。船头江水茫茫,商人少妇断肠。肠断,肠断,鹧鸪夜飞失伴。”温庭筠《梦江南》中的“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吕本中的《采桑子·别情》“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此外,林逋、晏殊、柳永、贺铸、周邦彦、曾布妻魏夫人、范成大、姜夔,以及《九张机》的作者和其他一些无名氏,也都有这类佳作传世。但是,综观历代思妇、言情题材的全部作品,其中不少充斥着浮辞艳语,缺乏真情实感。李清照却不是这样。她所描写的伉俪之情,不是轻飘飘的卿卿我我,也不是言不由衷的故作伤感,而是一种有着共同志趣的同志之好和入骨的相思之情。《醉花阴》、《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等是她的思妇词的代表作,也是词史上数得上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过人之处在于:(1)作为一个封建社会里的大家闺秀,作者能够抹掉自己娇嗔羞怯的面纱,越出“非礼勿思”的雷池,大胆地倾吐自己的感情,这无疑于为作品灌注了新鲜血液、赋予了新的生命;(2)这类作品的主人公思妇,就是作者自己,作者以其富有才华的笔。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更是此类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男尊女卑,痴心女子负心汉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类现象,不论是在民歌或是文人创作中,都有普遍的反映。曹植的《七哀诗》“愿为西南风,长逝人君怀。君怀时不开,妾心当何依。”这是比较早期的。到唐宋这类作品更加流行。但多数作者像曹植一样,是有一种君臣不遇或怀才不遇的寄托。纯粹写夫妻情爱的,文人中类似元稹、苏轼对妻子的那种沧海巫山和“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是少有的。他们在嬉笑游冶,眠花卧柳生活中写的大量思妇之作,没有多少可取之处。那些较有思想价值的,由于大多是男性作者的越俎代疱,他们摹拟思妇情态尚可维肖,抒写内心往往不易细致逼真。当然像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一首,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得那样细膩人微,也是不多见的。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强弱,常常取决于作者生活感受的深浅。在封建社会能够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是天大的幸事,而与称心的伴侣生离死别,又是人生的极大不幸。二者都是李清照的切身经历。封建社会的女子经济不能独立,人身没有自由,她们的一切都寄托在丈夫身上,嫁鸡狗尚且都要相随,不用说像赵明诚那样有品行、有才学的人,李清照怎么能不倾心相爱?我们从她描写夫妻情爱的作品里,可以深切感受到其中凝聚着饱满而真挚的感情,以及女子特有的对爱情细致人微的描述,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例如,《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首词堪称真切、深情、细腻、独到之作,其结句更耐人寻味:唯有一个女子才能把自己受到离愁的煎熬与风霜之于黄花的摧折联系起来。也只有一个女性作者才能感受到,一个青春少妇不仅她的容貌如黄花般雅洁婉丽,作为一个思妇,她的苦境又与黄花的命运极为相似。这样一来,思妇的形象和黄花的形象也就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黄花晚节香”,一个女子对丈夫的爱情,也应该像黄花那样临风傲霜坚贞不屈一一无疑这也是“人似黄花瘦”这一名句中所包含的女性特有的思想感情。
再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不是一个十分钟情于丈夫的女子,她怎么会有一会儿蹙頞、一会儿伤心,丢不掉、放不下的感情呢?没有这样的感情,任凭妙笔生华,也难以写出这样质朴而动人的文字。
李清照共写过三首《蝶恋花》,有一首除了其中“柳眼梅腮”常被援引,整首词不大为人注意: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一个换上春装的少妇,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和煦春天里,由于没有亲人陪伴,无心赏花观柳。她把枕头垫高,但高枕也不能解忧,白天斜靠在枕头上,首饰也弄坏了。该睡的时候,不能人睡,深夜一个人剪下灯花把玩。“夜阑犹剪灯花弄”,包含着思妇的多少难言之隐。其实也不用明说,当读者看到一个思妇手里拨弄着灯花,心里就明白了。杜甫《独酌成诗》曰:“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相传人们以灯花为喜事的预兆。思妇手弄灯花是眼巴巴地盼望着亲人临门的大喜事。作者的情思巧妙地寄托在思妇手中的灯花上了。这种思妇的形象及其特有的感情,男性作者是难以捕捉得到的。才思过人的曹植《美女篇》:“盛年处空房,中夜起长叹”中的思妇形象,就其鲜明性和感情的细致人微而言,也不免略逊一筹。

《凤凰台上忆吹箫》是写离愁的: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凤箫和离歌是传统的辞别曲,作者选用这一词牌本身就是为了抒发她的“离怀别苦”。离怀别苦是我国诗词曲赋的传统题材,这首词一方面受到建安七子中徐干的情诗《室思》之三“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的明显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含有比徐诗更加丰富细腻的情愫,这种情愫往往是一个身闭闺闱的女子特有的,没有直接生活感受的作家很难写出这种情深意绵的作品。我们从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西厢记》里多次运用李词表达崔莺莺的离愁这一点,可以看出李清照的这类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一斑。
负有盛名的清代诗人王士祯,在《花草蒙拾》里把李清照称之为婉约词派之宗,未必允当,但他以为她的婉约词“难乎为继”却很有见地。本文胪述的,一言以蔽之,也正是李清照独步词史之处。